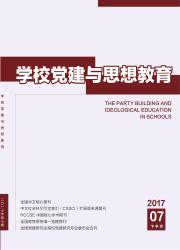
学生运动伤害事故司法诉讼现状 ——以归责原
一、学生运动伤害事故的司法诉讼现状
学生运动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负有管理职责的体育设施内以及由学校组织的与体育相关的活动中发生的,导致学校学生身体受到伤害的事故。学生运动伤害事故是学生伤害事故中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学生在校平均发生体育伤害事故为2.6次。在司法实践中,学校也常因此陷于诉讼纠纷,承担较重的责任。笔者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0日的398份学生伤害事故民事判决书梳理发现,学生运动伤害事故共有233件,占学生伤害事故的58.5%。在233起学生运动伤害事故案件中,学校涉诉的有207起,占比88.8%。法院判定学校担责的198起,占87.03%。在198起学校担责案件中,担责比例在60%及以上的108起,占46.79%,其中负全部责任的36起,占16.06%。
学校是公益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教育,但由于其涉诉纠纷多,承担责任较重,导致一些学校面对学生体育活动采取消极态度,长期如此将使学生在体育方面的受教育权遭到实质的剥夺,于学生,学校都无益处。
二、归责原则在学生运动伤害事故中的运用
在下文中笔者主要以李某与某中心学校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为例,就上述现状进行法律分析。
李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就读某中心小学五年级,2016年10月9日,李某在该中心小学体育老师的带领下参加县教体局举行的足球比赛中摔倒导致骨折。李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起诉要求学校赔偿。
法院判决:李某在足球比赛中倒跑其自身具有一定的过错,学校未就尽到教育管理的“注意义务”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公平责任,判决学校承担80%的责任。
在此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该法院认为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受到伤害,学校如未就尽到教育管理的“注意义务”充分举证证明,根据公平责任学校应当承担较重的责任。这明显有失偏颇。
(一)学校并非任何时候就“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三十八规定和三十九条规定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由学校就尽到教育管理义务承担举证责任,而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由受害人就学校未尽到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是指学校并不绝对的就“是否尽到管理责任”或者是“是否尽到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在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学校就证明其自身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责任较重。但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由于其自身对于体育运动风险已具备一定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当受到伤害起诉学校请求赔偿时,则需要受害人一方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在本案中由于李某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在归责时应适用过错责任,依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应由李某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学校在带领李某参加比赛时并未对李某进行安全教育告知和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而不是学校在任何时候就“注意义务”都负有举证责任,学校未就注意义务承担充分的举证就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
(二)当事人均无过错是公平责任适用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6条规定明确指出,公平责任的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均无过错。但在本案中,法院在认定李某和学校均有过错时仍适用公平责任,明显是法律适用错误,扩大公平责任的适用范围,使学校承担责任于理无据。但以上阐述也并非说只要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一定适用公平责任。是否运用公平责任还需看学生是否为学校的利益而致害,在本案中如果李某与学校均无过错的前提下,学校应就李某受到的伤害按照公平责任原则分担风险,因为李某是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代表学校为学校的利益参加比赛的过程中受到伤害,获利者应当分担风险。法官不严格的依照归责原则判案,无疑是加重学校责任。
(三)针对性法律欠缺,保险制度不完善
在本案中,还涉及对学生运动伤害事故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处理该类事故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人生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参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第九条到十五条。《体育法》并未就此规定。缺乏针对性法律对学生运动伤害事故作出规定,对学生运动伤害事故归责原则的适用在实践中出现不统一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善良的法官在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时自然会倾向学生,让学校承担较重的责任。
